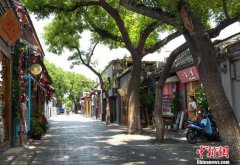|
名字是最显性的标签,呈现出你希望向这个世界传递的信息。 从5月以来,蚂蚁金服改了名字,外界能看到的是支付宝底端的tag上,原来的“蚂蚁金服”变成了“蚂蚁集团”。相比今年3月支付宝升级数字生活平台,这一变动略显低调。有信息显示,蚂蚁的全称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改为“蚂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两个变化值得划重点,一是去掉了区域特征,另一是突出其科技底色,从小微金服变成了“科技”。这隐喻着它的主战场将是一个更大江湖,即全球To B服务的万亿蓝海。 当我们抵达从移动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迁徙的分水岭,会发现两条主脉络。一条是从物理全球化走向数字全球化,突破产业链在空间结构上的摆布,构建一个没有国界,跨时空的真正全球化。另一条主线是由单一创新走向集成式创新。新一轮技术红利,更依赖5G、区块链、大数据、AI、物联网等多项技术集合成的基础设施,来激活庞大存量经济,提升全链条内部效率和对外服务能力。 不难发现,这与蚂蚁科技集团(下简称蚂蚁)发展轨迹完全契合。再向前观察,从其前身支付宝开始,除了表面上不断拓荒之外,还隐藏着两条暗线,即跨区域与技术化。这两条暗线铺垫已久,终于由暗变明。 疫情按下了快进键,蚂蚁在疫情中展示出了搬山之力,作为阿里数字经济体的金融基础设施,它能够打通线上线下,串联经济体之间的不同业务场景。 它为中小商家提供最需要的生存工具:钱和流量。2月10日,蚂蚁宣布了包括减免平台商家经营费用,提供资金支持,为商家提供低息甚至免息贷款六方面20项扶助措施。到3月2日,不足一个月,就有30万商家从网商银行拿到了利率8折的100亿特别扶助贷款用于复工复产;6月5日,打开支付宝首页,会看到线上烟火气十足的“地摊经济”。它新增“好生活”板块,以瀑布流形式展示各种生活服务——支付宝改版后强化了“中心化+去中心化”的模式,以中长尾商家更好渡过冷启动期,并持续增长。 蚂蚁集团CEO胡晓明曾在3月大胆预测,疫情之后,中国城市管理与公共管理效率将提升3%-5%,由此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的联动。中国服务业规模目前是53万亿,他预测5年后一定会超过65万亿,若蚂蚁金服能推动其中50%线上化,也意味约30万亿体系要数字化。 在蚂蚁向商家和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表面之下,技术更像肌肉层,它逐渐显性化,既受益于商业,又反哺了商业。更名,则意味着以更开放姿态输出力量的时点到了。将创新技术基于自身业务上试验成熟后再对外向B端开放,是蚂蚁一直的策略。在数据库、金融云、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等领域,都沿用此经验。 它从2010年开始投入自主研发分布式数据库OceanBase,彼时背景是“去IOE化”,经过阿里大规模场景、支付宝金融级场景以及双11等战役等炼狱般考验,OceanBase能用更低成本做到多中心多地域极限容灾能力,满足数字时代对服务永远在线的严苛要求,也能适应不断扩张的数据处理需求。它在2020年6月8日战略升格,成为独立子公司,胡晓明亲任董事长,号称3年内将服务万家企业。 区块链是蚂蚁集团另一个大杀器,它可能成为阿里数字经济体中下一个“阿里云”,根据全球权威知识产权媒体IPRdaily 发布的2017-2019年全球专利排行榜显示,截止2020年4月17日,它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区块链专利,共2344件。在共识机制、高并发交易处理、智能合约、可信计算、隐私保护、跨链交互、安全机制等核心技术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蚂蚁金服早在2015年就成立了区块链小组。区块链与支付宝的初心——解决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天然契合,蚂蚁希望将其进一步全面推进到数据、资产、物理世界的万物互联与多方协同,它所有落地场景都瞄准“生产级的联盟链”。 目前,蚂蚁钱包全球用户总量已突破12亿,支付宝已与全球250多个金融机构建立合作,网上支付打通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27种币种交易。不过,蚂蚁在国际上的技术形象,比金融形象更为突出。 2016年马云提出了e-WTP的构想,同年 9月写入G20公报,受到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欢迎。e-WTP为电子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简称,核心是通过公私合作,孵化贸易新规则,构建数字时代全球贸易基础设施。疫情中,欧洲多国航运中断,但比利时政府与阿里2018年共建的eWTP列日机场枢纽依然高效运转,成为中欧救援物资主通道。 蚂蚁则作为e-WTP的金融基建者,其野心是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全球买、全球卖和全球汇”、金融与技术服务。有菜鸟与蚂蚁在全球搭建的物流与支付基础设施,阿里新零售与全球化业务才能一路狂奔。 跨区域与技术化,这两条溪流终于与产业互联网的大趋势融合,进入大江大河。我们下面从三个切片,所触发的三个方向上的打通,来探究它今日基因的形成,和未来走向何方。 01 快捷支付之战 打通移动支付繁荣之路 在支付宝发展史上,2010年1月22日需要一个大特写,这一天,马云在年会上痛斥支付宝“烂,太烂,烂到极点”。关于年会细节,已多有报道,勿需赘言,如果仅仅截取这个瞬间,会令人觉得批评来的突兀而猛烈,当把镜头拉的更远,就能发现其实在年会之前,支付宝上下都弥漫着焦虑。 压力并非来自数据层面,截止2009年年底,支付宝用户总数超过2.7亿,到2009年12月8日,日交易额创了新高,达到12亿。这意味着不到十八个月时间,日交易额就翻了将近6倍。 焦虑情绪来源于支付宝第一次“开放”,即2007年逐步脱离淘宝的母体。这是一个揪心决定,湖畔大学教务长曾鸣回忆,当时淘宝跟支付宝打的不可开交,他加入阿里的前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协调淘宝跟支付宝的矛盾,到底是淘宝该支持支付宝向外扩张,还是支付宝应该先服务好淘宝的各种需求。 2007年9月28日到30日,阿里开了一次封闭的集团战略会,最后有一个定调影响了阿里之后十年,即“建设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支付宝“出淘”,由此获得了一面大旗。不过出淘之后,就失去了铠甲。支付宝创立之初,名为“支付保”,可见它最早做担保交易,而非支付,主要解决买卖双方不信任。服务淘宝很简单,内部对其担保交易模式也比较满意,但对淘外商户而言,它们需要面对与财付通、快钱、易宝支付等第三方公司的直接竞争。 此刻支付宝发现,原来自己在支付产品方面并无优势,不管页面设计还是付款流程,都还不如别人,最初只能拼费率,但彼时都已经拼到了千分之几,此方面空间已有限。 支付宝2009年决心要提升用户体验,专门搞了个用户体验部,从页面、文案、按钮、流程,上线了200多个功能。然而,沮丧地发现,支付成功率从年初的60%提到年底的62%,一年只提了两个百分点。 假设100个人要付款,最后只有62个人能成功付款,这个比率当时在全球已算领先,不过从用户角度,无疑感受很糟糕。那次年会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批判大会,马云只是上来补了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