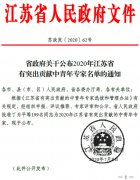|
2016年1月,河北邯郸的高雅宁驾驶特斯拉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以“自动驾驶定速模式”行驶。在遭遇位于前方的道路清扫车时,特斯拉车载人工智能却未采取任何紧急制动或避让措施,导致高雅宁径直撞上道路清扫车,并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作为我国首起基于人工智能的侵权案件,此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发生大规模的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但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其后或将有类似的案件诉至法院。因此,有必要就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进行前瞻性讨论,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以保障生产者、使用者及受害人的利益。 人工智能的定义 关于人工智能,目前学界有诸多不同定义。尤其在判断智能的标准上,更是有着极大争论。笔者认为,从机器到机器人,人工智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备了在数据交换的基础上完全的自主学习能力、基于具体环境信息下的自主判断能力,以及自主作出相关行动的能力。概括来说,人工智能是不需要人类介入或干预,即可进行“感知-思考-行动”的机器人。 至于基于人工智能设计的自动驾驶汽车的概念,各国规定也不尽相同。依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给出的评定标准,自动驾驶可分为6个等级。其中,第0-2级为辅助驾驶车辆;第3-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车辆(Highly Automated Vehicle,以下简称“HAV”);第5级则被称为无人驾驶车辆(Self-Driving Car,以下简称“SDC”)。 本文所称的自动驾驶,并不包括辅助驾驶。下文分析均基于第3-5级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下的交通肇事情形。 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的适用困境 (一)过错侵权责任原则适用困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归责以过错责任为核心、以无过错责任为例外。但是,在自动驾驶汽车侵权中,通常难以确定当事人的过错。 以特斯拉汽车为例,在启用SDC模式下,人工智能将独立接管全车的驾驶控制系统,而无需驾驶员进行任何辅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驾驶员已经完成了由司机到乘客的角色转变。那么,当发生交通肇事时,若法律将过错归责于驾驶员,则与发明自动驾驶汽车的意义相违背。同时,也将对驾驶员造成极大的不公平,因为这将使其对非因自身过错导致的结果负责。但是,若将过错归责于生产者,也难以自圆其说。究其原因,事发时,人工智能系统是基于自我学习感知而作出的行为,生产者本身并不干预人工智能的具体行动。 (二)产品责任难以举证 当侵权受害人无法以过错责任要求驾驶员赔偿时,理论上似乎可以引用产品责任的无过错原则,以产品缺陷为由,向生产商、制造商追偿。但是,在实践中,该追责方式同样极为困难。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受害方负有证明产品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但就自动驾驶汽车肇事侵权案件来说,证明其外部机械设备制造缺陷较为容易,证明警示缺陷也有可论证空间。但是,若存在内部的人工智能设计缺陷,由于其技术的高精尖性及不可预测性,受害方很难证明该人工智能自主学习后的程序运行结果是有缺陷的,更难以进一步证明该算法运行结果会有“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且其后天的学习不为初始制造人员所控制,所以,仅从技术层面论证,很难将责任归咎于生产商。生产商甚至还可以援引“开发风险”抗辩或以“技术中立”来主张免责。 (三)人工智能本身不能成为责任主体 有学者指出,既然无法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过错责任与产品责任,那么,能否由人工智能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目前来看,这个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只有法律主体可承担法律责任,而人工智能尚不具备法律人格,无法成为法律主体,故也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若想调整和规范人工智能侵权问题,需对现行法律规则作出进一步完善。笔者提出以下构想,以供讨论。 明确自动驾驶下的风险分担原则 由于人工智能无法独立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当自动驾驶发生交通肇事时,在无法直接适用现有《侵权责任法》的前提下,应当将产生的风险进行分配,以明确侵权责任。 (一)风险控制原则 依据风险控制原则,当某些日常活动存在一定危险性、有损害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风险时,为了保障社会安全秩序,必然需要相关人员对其中的风险加以控制。该相关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需对特定事物或活动的危险有一定了解;当危险发生时,相关人员需有控制风险的技术或能力。在此情况下,因特定风险引发的损失应由控制该风险的相关人员承担法律责任。 在HAV状态下,机动车的驾驶员或所有人均能对驾驶活动所存在的风险予以一定控制,因而法律有必要赋予其警示义务。在此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的驾驶员或所有人均应依法对由风险引起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在SDC状态下,基于驾驶员对完全自动驾驶的合理信任,以及发明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本意,法律可不强制要求驾驶员负有警示义务,驾驶员此时无需对损失承担最终责任。 (二)危险开启原则 危险开启原则认为,存在危险的日常行为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危险本身是被法律所允许的,危险活动的开启人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如果有关人员存在过失,则危险活动的开启人为责任主体,应承担责任。 在HAV和SDC状态下,驾驶员使用自动驾驶系统,会在原有基础上给社会增加一定危险,属于开启一种危险活动的行为。由此,在HAV状态下,若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存在过错(如未合理注意),则其应为事故的责任主体;而在SDC状态下,驾驶员虽并无警示义务,但基于其危险开启人身份,也应与生产者共同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三)报偿原则 报偿原则认为,给予每个人其应得的东西,乃是“正义”概念的题中之义。“应得的东西”既包括正面的利益,也包括负面的罚则。该理论应用于民法领域,即当民事主体进行活动或负责管理某物时,其在享受该民事行为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伴随而来的风险。 在自动驾驶状态下,首先的受益者是驾驶员。当人工智能为其服务时,驾驶员既解放了双手,又能到达目的地。但是,考虑到驾驶员(或者说车辆所有者)已在购车时就付出了相应的购置费,因此,可以认定其已提前为自己所受利益“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