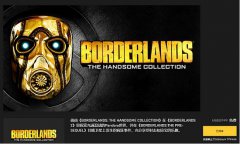|
他说,相对而言,中职学生学习自律性更低,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中认真学习在线课程,只有少数学生能做到自律。三年级学生面临中职生对口升学考试的压力,学习效果好于一、二年级学生,但没有学校环境的学习氛围,学习动力明显不足。 “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分散注意力,如家长递水杯、送水果、直播视频的弹幕、手机或电脑的其他软件消息等。”高一轩说。 因直播而产生的新的教学困扰,成为疫情期间老师们热议的话题。有老师说,小小的屏幕,限制了师生间“心心相印”的感觉;也有老师觉得,自己讲得全情投入,学生却听得断断续续,讨论交流、随堂互动很少,网课基本上是“两张皮”。 顾小曼(化名)直言,自己没有参与直播,只是定期上线讲解学生课堂中没有听懂的内容或者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却得不到学生及家长的全力配合。 “主要原因在于家长的教育意识相对欠缺。”顾小曼说,在其所在学校,不少家长认为自己没怎么读书,也没饿死,所以并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 “一个学生长期不交网课作业,我联系家长后才得知,孩子在奶奶家住,奶奶不懂,不让看电视,家长外出打工又带走了手机,所以孩子几乎没有上过课。”顾小曼举例说。 直播过程中,她还不时会听到学生家里此起彼伏的鸡叫声、鹅叫声。在恢复交通后,她曾去学生家里家访,却发现,本该上课的时间,学生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儿了。 期中测试,学校组织教师将试卷送至学生家中,要求家长配合监考。考完试后顾小曼研究试卷发现,有个别学生收获颇丰,多元的教学方式启发了一些思考的角度,课外阅读及习作能力也有提高。“多数学生态度敷衍,答卷草草了事,还有部分学生试卷中出现了家长的字体”。 开学后测试班上学生成绩两级分化明显,在广西梧州市一所高中,青年教师张霄(化名)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一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往往经常旷课、随意开小差,各种状况层出不穷,教学效果降低也在情理之中。”她反思道。 网课期间,为了弥补线上教学互动不足的短板,张霄有时候也会给家长打电话、发微信,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可她后来发现,网课期间很多学生用的是家长的手机,“一些孩子会偷偷挂掉电话、删除聊天信息”。 “复工复产之后,大多家长忙于工作,更是没工夫监管孩子。”张霄所在的高中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全在学校,网课中她发现,平时习惯了有人鞭策、敲打的学习模式,一上网课,学生们就像“放羊”一样。 “调研发现,疫情对中小学生学业的影响,与家庭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关系较大,这样的差别在城乡学生身上体现较为明显。”西安交大上述课题组的调研显示。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付卫东分析,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学历普遍不高,这类家庭的孩子在缺乏家长监督和学习辅导的情况下,在面对手机游戏和网络诱惑时,容易沉迷其中,耽误学习,造成成绩下滑。 上网课也给部分教师带来挑战 与此同时,上网课也给部分教师带来挑战。 中国教科院的调查表明,在线教育支持度和满意度与教师学历、信息化教学能力呈正相关,与教师年龄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教师越年轻、学历越高,信息化教学能力就越强,在线教育的效果越好。”付卫东说,对比东、中、西部三类地区,西部地区教师平均年龄最大、平均学历最低、信息化教学能力也是最低的。 即便是青年教师,首次面对镜头,也多少有些陌生。“对直播软件的操作不算熟练,也不知道屏幕后面除了学生还有哪些人在听课,总觉得有点不自然。”刘昵娜说。 因而,为了上好网课,很多老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挑选更适宜于教学实际的直播软件,参加学区、学校组织的直播技能培训,私下反复摸索,甚至让家人、同事当受众,提前试讲,测试直播效果。 不少教师表示,由于直播中无法根据学生的即时反应调整课程内容,教师讲课的主观性更高,因此网课教案、PPT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还要尝试用更有网感、更亲和的话术,拉近和学生的距离。 李悦还记得上第一堂网课时,数学老师准时开讲,一来就熟练使用连麦功能,不时在群里提问互动。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老师在课间用方言问起了同学们的寒假生活。有几个调皮的同学,还把老师讲课的情景,做成了表情包,在班里的QQ群悄悄传播。 即便在努力适应新挑战,可张华还是觉得,线上课堂和线下还是不一样。“线上上课时感觉对课堂的掌控力不强,需要刻意地去维护课堂秩序,而线下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贯穿与教学当中,上课更加行云流水。”他说。 网课“后遗症” 返校后,在线教育的“后遗症”随之显现。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采访中,大部分老师表示,自己所在班级的平均成绩有所下滑,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趋势”:即优生学有所获,开学后处于“喂不饱”的状态;原本依赖老师监督管理提抓成绩的中等生分数下滑;后进生中,只有个别学生得益于家长监管,成绩有所提升,相当部分有厌学情绪,甚至会自暴自弃。 学生的不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节奏。本着对学生负责的初心,不少一线教师通过补课、复习等方式,对网课内容重新梳理。 甘肃天水一所城郊中学青年教师李岩(化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目前,他所在的学校,调整了初三学生的课表,将每天7节课变成了9节课,早上6点半加开早早自习,下午的课程也一直持续到6点40分,“尽可能多补点,让学生在中考中获得一个好成绩”。 “全力精心准备,40多天的网课只是感动了自己,却没有完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着20多年教龄,对于眼下学生直线下滑的学习成绩,资深中学教师宋萍萍(化名)也很无奈。 开学后,宋萍萍找学生谈心。可不少人却直接告诉她,反正自己要去读职高,老师就不要再费力气了。“实际上,这些学生是因疫情期间功课落后太多,觉得现在努力为时已晚,便选择了逃避。”宋萍萍说。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入职以来,李岩习惯用一种“亦师亦友”的状态与学生相处,在日常教学中,除了提抓成绩,也注重培养同学们的学习习惯。 “超长假期”却让学生比平时松懈了许多。“需要我专门指出来,一部分学生才会动笔做笔记。”李岩发现,复课后,班里学生对他的信任感变淡了,课堂表现也不比以往,养成的好习惯也丢了大半。 更令他担忧的是,有少部分学生对手机产生了依赖,还不时因手机与家长产生冲突。“家长打电话过来,希望老师严加管教,但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期,但凡稍加训斥,他们就会逃课、逃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