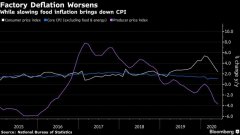|
刘爱琴: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他内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问我怎么熬过来的,具体我也说不出来,但那时就是有个念头——不能死。那些人诬陷我父亲和家人的(内容)我一个字也不信,我坚信真相总会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报:从父亲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这个念头支撑你? 刘爱琴:经过文革,我母亲这三个孩子就剩我一个。有个场景一直反复出现,我们老家是湖南,当地的农民写信给父亲反应农业生产的问题,他都一封封亲自回信,还托人带话说如果农民写字不方便,就直接来找他说。政治上的东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是会被后人知道的。 晚年 希望我的孩子远离政治 新京报:父亲被平反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刘爱琴: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太长了。反正是该等的等到了。 新京报:之后你写了关于父亲的书? 刘爱琴:有出版社联系我,后来就写了《我的父亲刘少奇》,算是一个追忆和怀念。 新京报:你的人生很多时候被父亲决定和牵连,加上他的严厉,心里有没有怪过他? 刘爱琴:父亲始终是父亲,他的很多决定,在他的角色看来,有他的理由。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没有怪过他。至于牵连,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父亲的错。 新京报:经历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不是刘少奇的女儿、我生在寻常百姓家就好了”? 刘爱琴:怎么不想?想过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一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我也没觉得,是刘少奇的女儿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这个。 新京报:心里没有怨恨? 刘爱琴:怨恨谁呢,时代造就的悲剧,早就看淡了。几年前我还回过一次内蒙古,和文革中审查我的人一起吃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心里没有怨也没有恨,都过去了。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如何? 刘爱琴: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上次俄罗斯大使馆发完纪念章,第二天我们就聚会了,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大家都用俄语交流,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 平常我特爱遛弯儿,早几年,清早5点就起来,坐地铁到颐和园,溜达一大圈儿。也喜欢看书,最近我总谴责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动太多,好久没看书了。 新京报:几个孩子呢? 刘爱琴:他们都长大了,最大的已经60多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家有第四代了,快一岁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报:会愿意小辈们从政吗? 刘爱琴:不愿意。我父亲以前总说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辈子,我也没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远离政治,平安开心地生活,就很好了。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