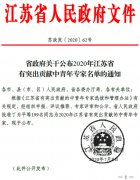|
2020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对于刚刚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来说,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要确定报考的院校以及相关专业。鉴于近半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国内各高校纷纷开设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相关专业,今年的高三考生中,未来会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公共卫生领域。 今年的高考考生多为2002年前后出生。当2003年非典暴发时,他们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恰恰是非典过后,国内的公共卫生领域迎来了一波发展高峰。 17年足够一个婴儿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但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建设工作来说,这17年的发展却难言满意,近两年甚至有萎缩的态势。而新冠病毒的来袭则为其又带来一波热潮。 然而,热潮总有退去的一天。届时,此刻即将迈入公卫领域的学子们,又将面对怎样的现实? 数量问题:人才缺口有多大 提到近半年来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所面临的机遇,一个直接的证据便是国内高校纷纷成立的公共卫生学院(以下简称公卫学院)。 根据媒体报道,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已有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新余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湖南医药学院等一批高校发力公共卫生领域建设。其中,成立于7月7日的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为截至目前最“年轻”的公卫学院。 大量公卫学院的成立,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公共卫生相关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这也正是目前公卫领域最为乐见的一个现象,毕竟,我国公卫人员规模不足已是一个老问题。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目前,我国约有100所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或预防医学系,约70所院校培养硕士研究生,约30所院校培养博士研究生,每年输送公共卫生人才约7000名。这一数量似乎不少,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则相形见绌。 据统计,截至2018年,中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业人员约18.78万人,每万人口中仅有1.35名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这一数量仅为美国的1/5。2014年,我国在颁布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中,要求疾控人员按1.75/万人进行配置,但目前相关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达不到标准。 如此看来,国内公卫人员数量出现缺口已是不争的事实,高校大力培养相关人才也是题中之义。然而,以上数字并没有说清一个问题——国内公卫人员的缺口究竟有多大?事实上,在记者查阅的所有相关文件及报道中,均未看到这一数字。 “我国公卫人员的缺口肯定是有的,这点毋庸置疑。但具体缺多少,的确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调研。”受访时,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程彦斌坦言,国家层面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对未来几年国内公卫人才的需求进行评估。针对目前体量和未来需求之间的差距,有关部门要出台指导性的意见,高校据此进行招生及教学安排,“招生时要和其师资、教学资源相匹配。” 然而截至目前,至少在公卫学院的建设以及学生培养数量方面,有关部门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和指导。 早在多年以前,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在西方,高校在专业设置、招生数量等方面的自由度非常大,政府并不干预。但针对医学生的培养规模和结构,政府会严格干预,大学不能自由招录。反观我国,很多方面都控制得很严、规划得很好,但恰恰在医学生的培养方面,虽然有规划,却规划得不到位。 “我国地大人多、社会结构层次复杂,而培养医学人才是一个庞大工程。”熊思东说,这决定了医学人才的培养是需要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的。“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口径的医学人才?培养什么样结构的医学人才?换句话说,我们的医学人才数量和结构如何来平衡?具体如何设计、如何规划?这些都需要提前筹谋。” 结构问题:培养体系如何纠偏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公卫人才培养规模不足的问题其实就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扩大培养规模之声也已经出现。例如,今年2月,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就曾撰文,建议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由医学院校设置公共卫生相关专业。 这份曾引发公众普遍关注的建议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我国公卫人才素质普遍不高。 《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及以下的比例高达23.4%;技术型、管理型专业人才严重欠缺。以湖南省为例,该省《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3—2018)》显示,2017年,湖南省级疾控部门的卫生技术人员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68.86%,研究生学历仅占3.16%,中级及以下职称占92.61%。 针对这一问题,近期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发声。如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息凤便曾对媒体表示,要加强不同层次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既培养可在基层卫生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的技术性人才,也应该培养层次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术型+研究型人才,如研究型、专业型硕士及博士生培养。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参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相应的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然而,培养不同层次公卫人才的职责,是否也需要一定的“分工”呢?在程彦斌看来,这一问题牵扯到目前我国公卫人才除数量不足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现状,那就是人员结构的失衡。 “目前,我国县一级疾控部门基本没几个专业的人才,但高校培养的大量人才却出于各种原因,很难‘下去’。在我国西北地区,甚至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正规的公卫专业大学毕业生。”程彦斌说,相比之下,在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以及省市一级的研究部门,公卫人才缺乏的问题要相对好得多。 这说明我国公卫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结构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不是仅仅依靠高水平大学就能做到的。 程彦斌坦言,高水平大学在公卫人才培养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扩大其招生规模也自有其道理。但是,这类高校扩招的总数不能过大,“因为它们培养的都是高端公卫人才,而这些学生是很难真正下到基层的,一味地扩充反而容易形成资源在局部的过剩。” 他表示,目前公卫人才培养的主要发力点还应放在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毕竟这些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才能够真正扎根地方,从基层提升我国公卫人才的整体素质。” 流失问题:拿什么留住人才 数据显示,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我国公卫人才培养曾出现过一个热潮。例如,2004年,我国疾控团队的人数曾达到创纪录的21万人,很多学校也建立了预防医学专业。然而自此之后,相关人员的规模便呈逐年下降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