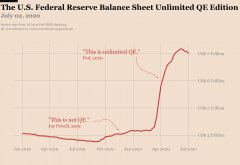|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同年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启事中还登出了十九个发起人的名字。这十九个发起人,后来几乎都成了共产党员。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在这一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灿烂之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十月革命影响,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德国、匈牙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曾一度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马克思主义最终没有成为这些国家思想的主流,而在离其诞生地十分遥远的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严密的科学之外,还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艾思奇曾就此做过精辟论述:“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第26号,1939年4月28日第6版)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不只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很多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不但不感到陌生,反而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一见如故的感觉,从而激活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里原本就有的追求和向往大同社会之基因。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在回顾自己思想转变时曾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8—1059页)正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思想共鸣,诞生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不变的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根来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责编: 王东) |